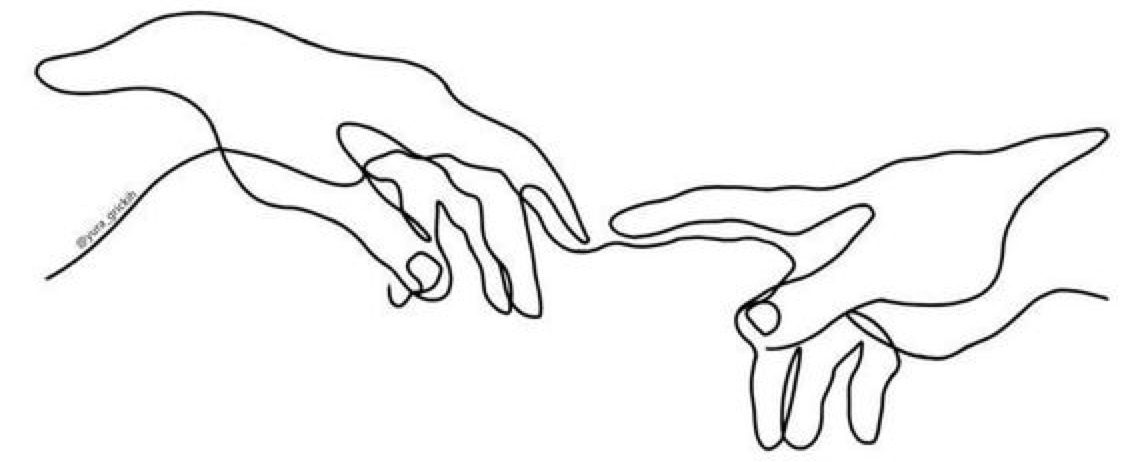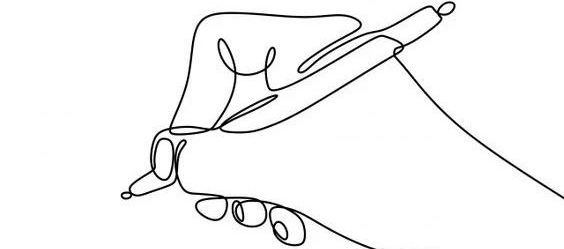去年参加了一个作者的采访,她当时正在筹备一本书,书的主题是在中国和印度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对于婚育的态度。她是一位在香港长大的印度女性,很明显对于中国有一些近距离的观察和了解,但又与像我这样切切实实在那个环境中出生长大的人不同,我潜意识里知道她是一位局外人。对女性议题的私人兴趣是我接受这个采访邀请的初衷,不过当时我内心还有一个隐秘的心愿:As a Chinese feminist, I want my story heard in front of the potential global audience. 刚走进采访会议室的我就已经明确了自己的角色:作为一个中国女孩,我要向一个陌生人分享一个我的故事。
那么问题来了,我的故事,由我自己讲述的过去,我会怎样讲述它?
整个采访时长90分钟,作者从一些很开放的问题问起,比如我怎么看待和描述我的童年,我在中国的读书生涯等等。我给她讲述了我从小学到高考,再到大学的整个变化和心路历程。就像许多中国小孩一样,我从小就被灌输高考决定命运,一直拼命学习;同时作为一个女孩,我被告诉我没有男生聪明,一直深陷对于成绩一落千丈并被男生赶超的恐惧中;家庭和学校的教育并没有让我准备好去面对大学生活,大学的压力与迷茫当我无处遁形……在谈论这部分过去的时候,我非常熟练,就像我准备好了稿子提前彩排过很多次一样。我当然并没有为这个采访准备任何东西,只是这样的setting足够standard:一个高考幸存者去谈论自己的应试教育史,同时穿插着被男强女弱的父权迷思的毒害史。过去几年,我一直在用这样的视角和关键词去重访、谈论我的过去,跟我亲密的朋友心中一定有我谈论起复旦时脸上的厌恶神情和traumatized情绪。这样一遍遍谈论多了,视角就被固定。我已经为我的那段过去建立了一套稳定的叙事,在那个采访中我只不过是复述了一遍熟稔于心的标准答案而已。
采访结束后,我问作者目前的受访者都是什么样的,她说我与她们的故事惊人地相似:独生女儿,从小学习优秀,性别观念在中学左右开始萌芽,遇到学校和社会里的刻板印象:比如男孩子更聪明,女孩子普遍成绩更好,这只是因为她们更勤奋。最后她还谈到所有受访的女生都不愿意回到中国生活。诚实地说,在听到自己与其他女孩的经历100%相似的时候,感慨女生处境之余,我有一种羞于启齿的慰藉:我的感受和故事被分享了,我准备的标准答案得到了实践的检验。但我内心深处对那次采访的评价并不高,觉得差点意思。She could have asked further and dug deeper, and that narrative which I have told over and over again wasn’t the story that I wanted to be heard from the beginning.
这件小事以及随之而来的细微感受很快就淡忘了,直到这次春节回家翻出我从前的日记本,有许多东西渐渐浮出水面,这段已被遗忘的采访经历也在一次洗澡的水流中哗然进入我的思绪。电光火石之间,我突然有了顿悟,促使我写下这篇文章。
日记本带我重访过去,让我意识到我如何低估了它。在应试与内卷的刻板印象之外,我那段蒙尘的过去还有许多鲜活的复杂性,这得益于独属于我的乐观和顽强,也是我在叙述自我历史的时候被悄然忘却的部分。
高考备战的那几个月,我写了很多:
「这几天心绪很平静,喜欢在闲暇时瞎想,越来越多的是关于梦想。突然发现,自己的生活好像与他人无关,无论我的未来怎样,都仿佛是他人口中的一个故事,“他最后考上了清华”“她最后去了北大”都只是轻描淡写的一句话而已。 所以我想现在的我能能够活得更好,更有意义,不为别的,不是他人口中的一个平乏的结果,是为自己的生活创造意义,为自己赢得日后回想时的感动,为自己播撒进取的种子,感受汗水浸润之时的痛与笑,欢与泪。 最重要的几天突然来临,我想平静地接受风暴,写下我自己厚重的只有自己了解的意义与故事。」
「写下上一段话后,就不知该写什么了。心情突然好了。我突然明自,写日记真的不是为了记录感受,为以后勉励(这个本子上都是心情不好时写的),而是为失落的自己寻找问题的答案。写着写着,答案就有了。或许每篇结尾都是正能量的规律让人觉得好笑,可最起码答案是来自心里的。」
还有许多类似的文字,尽管稚嫩天真,跃然纸上的是一个善良乐观的小女孩。读下来觉得那时的我虽然客观上处在一个toxic的环境里,我主观上并没有深受其害。一些家人朋友具体的爱与关怀也被记录了下来,那段岁月还有其温暖可爱之处。
那么,我在采访里分享的那段过去是真实的吗?如果是,是多大程度的真实?
我当然没有在采访中撒谎。只是不撒谎并不能抵达真实。在这里我想表达的真实,genuineness,还蕴含着那些未被诉说的部分。历史是主观的,叙事是主观的,这是我在复旦的历史课上学到的。Who lives, who dies, who tells your story? 故事讲述者的权力,这是我在高二看汉密尔顿时学到的。是的,说到复旦,复旦留给我的不止有创伤,也为我带来了许多启蒙。比如我还记得大一的《性别与历史》课上,我坐在光华楼一楼的阶梯教室里听到陈雁老师说“我们要区分sex和gender”“性别是社会建构的”时的震撼(原来我大一就开始接触女权了?);在《法制与公民》里听张晓燕老师讲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,知道了“公共”这个词到底在说什么;在《美国文学选读》里读迷惘的一代,垮掉的一代,记得那学期读了好多福克纳的小说,痴迷于他的意识流文学;在新院读了很多诘屈聱牙的文献,走马观花地读了胡塞尔、拉康、拉图尔等硬货,埋下了许多观念的种子。
当高三那些苦中作乐的温情时刻,以及在复旦读书时迸发的许多思考碎片被过去留下的文字唤醒时,我深切意识到我对自我过去的认知视角被框住了。我对于我的高三和复旦生活已形成了一个“标准答案”和一个稳定叙事。而叙事的形成受制于一些视角,比如对于应试教育和内卷文化的批判,我带着这样的批判眼光去看待我的过去,讲述我的历史。对于那些不符合这个叙事,甚至看似矛盾的部分,都被我忽略,进而被渐渐遗忘了。
但我过去的日记告诉我,翻开那些看似矛盾的部分,接受发生之物的复杂性,才是对自己更诚实,更能体现主体性的一个选择。...